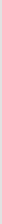葛剑雄:上海《探索争鸣》杂志要开一个会,主题就是围绕所谓“公共史学”,让我发言。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概念抬高了,什么叫“公共史学”呢?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 发现所培养的历史专业研究生就业很难,因为大学里要不了那么多专门的历史研究人才;于是认为他们的出路在于到社会上去,比如到企业,甚至到社区里去工作。美国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“公共史学”观点,并带头在高等教育里开设了公共史学课。
美国人有一个特点,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让一个事件“名正化”、“学术化”,提出一个模式、一个框架。比如说我们强调历史一定要应用,怎么应用?他马上就弄出一个“公共史学”的概念来。
其实这是历史应用,我们中国比美国早得多,以前中国的师范大学培养的历史系, 学生们就是准备做中学教师了。我们今天的研究生,大多数都已经是中学的学校教师了。这有什么了不得呢?国内有些人不懂,一种人认为“公共史学”这个概念对我们有用,可以用。另外一部分人认为“公共史学”是大众史学,等同民间野史,要让它来冲击学院正统的史学观念。
现在又炒作“公共史学”这个概念,媒体采访我,现在“公共史学”对你们历史专业有什么冲击?我说这是笑话。这有什么冲击呢?难道我们历史出路要靠公众吗?用不着的。所谓公共史学,最多就是我们讲应用史学,就是历史讲要重视运用,就是这么回事,改了一个新的名字,国内反正不要叫“公共史学”。
我发言就讲,所谓“公共史学”冲击传统史学这个观念是错误的,为什么错误呢?世界上,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历史, 英国人也要修 《大不列颠史》,不是你公众把关的。官方历史是国家、政党引领你的史学,而不是公众引领你的史学。
从学术上说,当然我们学术界引领你,对吗?有些人就像民间科学家,认为他比我们高明,用所谓的“公共史学”冲击传统史学,你怎么冲得了我们?到现在为止,传统史学里,哪些东西是我们专业人员记错了,要靠你来改写发现冲击的?不可能的。
又有人说,我们需要重视 “公共史学”,谁不重视?中国历史上,古代人都有这个传统,皇帝修史以外, 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留下许多民间的书籍记录。这套东西中国早就有了,重视口碑资料,这还要你们现在反复强调吗?
张英:每个国家都有官方历史,国家历史,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。
葛剑雄:不管哪个国家, 历史本身都是意识形态,是出于国家利益、民族利益,有选择的记录,有意识的记录。
现在媒体捧的所谓历史学家, 历史学界都不承认的。这就是“公共史学”的行为,好像社会上谁的声音响、谁的力量大,声音响、嗓门大,影响的人多,谁就是真理。
公众往往都是盲从的,比如说评价陈寅恪,我曾经写过文章,很多人把他捧到天上,这些人看懂过他的书没有?好多人都没有看过,看都看不懂的。
张英:也是制造神话。借古人今用,浇灌心中块垒。你批评过季羡林,认为他不是国学大师。
葛剑雄:我是对事不对人。作为知识分子,说真话是天职。我有一个原则:谈事说人,尽量在当事人活着的时候,可以商讨回应,把事情说清楚。该批评就批评,我不愿意现在不说,等人死了再来讲,这不道德。
比如,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吗?大家都知道,他最擅长的是印度的梵文,懂十几国外文,学术研究也在这方面。你把他捧为国学大师,当然不合适。他的学术贡献,不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方面。后来季羡林接受外界记者采访回应说,有人说我不是国学大师,我当然不是,真的不是。
什么叫“公共历史”?没有“公共历史”的。如果你已经具备了历史研究的资格了,那就是历史学家。他就不代表公众了,只代表你个人。公众从学术上讲,是需要专家去引导的。
很多历史书,是根据典型,一个点、一个现象写出来的,而不是根据全局和数据论证写出来的。大家的思维单一,所谓的典型调查,是故意选择的角度和案例,左右方向,给出人为需要的结果。
比如你说现在学生厌学,不念书,那我去调查一个念书好的学生,请看,读书的人很多。放着专业的社会学方法不用,或者走形式主义,为设置的目的选角度,去取样,这些结果结论,都不靠谱、没有公信力。
今天有些人找我来谈宋朝,说如何伟大、发达,我是不相信的。
我不研究宋朝,但是我生长在江南,全国最发达的地区。我就不信宋朝的江南比现在的江南更好。宋朝底层社会的东西,你们去研究过了没有?做了多少数据分析?有没有数据比例?当然媒体没有人力和财力物力去做这些事情。
从谭其骧的研究生到助手
张英:当时为什么没去北大,留在上海读书?
葛剑雄:考研究生的时候, 我本来还想到北京的,家里人说,你刚结婚,总得考虑考虑家庭吧。我想想看,也对。那个时候市北中学还给我开工资,在职研究生嘛。到北京,肯定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女儿是我念研究生的第二学期出生的。
当时我还是有顾虑,读书要避开思想、文学的东西, 想来历史是比较实用。上海几个招研究生的老师,要么是思想史专业,要么是近代史专业;纯的古代史专业,老师不是很有名。算下来,考复旦只有历史地理比较好。
我当时还不知道历史地理, 我觉得我对地理很感兴趣,对历史也很感兴趣,就这样选择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。而且我对谭先生有点好感,他的照片曾经放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先进人物宣传栏目里,他是1961年还是1960年评的全国先进人物。我在中学的历史教程里看过一本历史地图的内部本, 这个老师了不得。我那个时候是上海人大代表,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有谭先生,所以就考他的研究生吧。考了以后,觉得历史地理很适合我。
张英:谭其骧为什么会把你选为助手?
葛剑雄:我是学校安排的,我愿意,谭先生也通过的。谭先生是这样的,很开明的,总是鼓励我们探索求新:跟他有不同的看法?我们再来讨论。有什么不同的问题,但问题要两方面看,我也明白这一点,所以不管学术上,还是工作中,我们都是开诚布公、直来直去的。
在一些事情上,我觉得有些是谭先生不对,我也是告诉他的,他也能接受的。有的时候,谭先生对事对人有些意见, 我会提醒他, 你要自己去调查去了解,不要听他人的判断和说法。有什么意见,我主张跟老师要当面提的。
当时,谭老师家住在淮海路,学校两点钟开会,我们一般十二点半就去接他了, 那个时候也没有高架路,堵车严重。他午觉都睡不成,意见很大。师母就当着人谩骂什么的,我后来就跟他提意见,谭先生你这个话不好这么说的,这个也没有办法,谁叫你家里住得那么远呢?而且你家里有保姆,回家就可以吃饭休息。我们家里没有,开会完回去要接孩子放学,回家做饭吃;有时候去晚了,孩子就一个人坐在学校门口。
本文由公号@哲学之路编辑发布
后来师母老年痴呆了,一看见人上门就骂,烦死了。有一次学校的党委书记上门,她也在里面骂。我就进去跟师母说,你这是什么话?领导到家里谈工作是照顾谭先生,你不让领导来家里,不是就要叫谭先生跑远路去学校?这是学校里的规定,不愿意工作,那么就退休,没有工资了。这样讲了,她就听了。
工作和生活的事情,我和谭先生分得很清楚。每次外出, 我都会跟谭先生说清楚:今天这个是公家饭,单位报销;今天这个饭是私人活动,每人多少钱,你该拿多少出来,从来没有什么不愉快的。我后来有一年到美国去,换成另外一个师弟做谭先生助手,我就把这个经验告诉他。
张英:你是有经验的,摸爬滚打,十年社会人。反而师生关系处得好。
葛剑雄:很多师生关系,就是钱的关系,没有原则,给闹坏了。好多师生关系不好,就是出在经济上面,包括发表文章,谭先生写了文章,我经常给他跑腿帮忙,他分稿费,我一般都不拿,偶尔适当拿一点。有的时候文章是我写的,谭先生就全部给我,我说不行的,要是我自己写,拿不到那么多稿费。谭先生还是要拿一点,但我拿大头,你拿小头。
我们这样讲清楚, 反而大家的关系, 始终都很好。老师叫你代买什么东西,你回头就给他报销就是了,不要他忘了你就不说话,自己倒霉。最后,类似的事情多了,大家都不开心。
比如我们写《中国人口史》和《中国移民史》,都是多人合作。刚开始合作,我就立规矩,讲清楚:这个书出来,丛书的名称和单本书的名称,怎么署名?按照每个人的劳动产出,分配稿费和版税。丛书出来,我挂名主编,不拿主编费;将来得奖,所有奖金,不管每个人写得多少,平分。个人单本,你拿你写的那本书去评奖,获奖了我不拿你一分钱,这都是你的。还有上海颁的奖,就是上海的参与者分;教育部全国的奖,所有参与的组织都平分。全国的奖状,如果就一份,留在我这里,其他每人一份复印件,我在上面签名,你也是其中一分子。原则和标准讲清楚了,最后没有任何不愉快的,人人都心安。
后来学校来取经:搞大项目什么经验,我说事前把规则讲清楚就好。参与项目的每个人,都在规则上签字,将来出来成果怎么分?署名怎么排队,后面怎么处理,大家都知道。我们高校社会上,集体合作,都是很优秀的学者,但缺少最基本的社会经验,很多合作弄得不愉快。西方就很讲究这个, 他讲究团队合作,他找一个人参与,还要看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经验,执行力就很高。
你看西方的高校,那么多项目,也是教授和学生合作,都是契约制,把规矩和分配机制讲好的,要签合同的。老板去申请项目,搞到钱,然后交给学生去做,会讲清楚,有的项目署名,有的没有署名的,利益怎么分配,他们都知道。所以不像我们这边,有好多麻烦、风波出现。
师门传统与“开宗立派”
张英:你怎么看待学术研究里的师门和流派?采访你之前,我们看了你和学生合作的一篇论文,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五十年梳理,把你们这个学科和门派还有师承传递勾勒清楚了。从历史地理学科来看,从顾颉刚到你的老师谭其骧,一直到你们,算是三代。
葛剑雄:中国以前是这样的,书院、学堂教育都是这样,某个学者、前辈创办学堂书院,都会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,然后助手和学生加入,在某些研究领域里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色,有了自己的理论特点和研究方法,逐渐形成了“开宗立派”。在学科、学术研究上,所谓的“师门”,本身师承关系还是很重要的。
顾颉刚先生说,我是只开风气,不为师。所以他的学生里面,做各种学术研究的都有。其实历史、地理不是他的特长,历史地理学是后来谭其骧、史念海、侯仁之这几个学生发展出来的,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。
谭先生算是兼通两边的,后来到浙江大学,历史和地理是放在一个系的。史念海先生他主要还是历史的,对吗?侯仁之先生是很典型的师承,跟着顾先生拿了历史学的硕士,然后出国到英国,念到了地理学的博士,再回来任教,是中西方教育结合比较好的,后来人家承认他是地理学家。后来谭其骧和侯仁之两个人,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了院士。
顾先生大批的学生都是搞传统历史的,后来到了谭其骧、史念海、侯仁之这三家做历史地理学,实际上又互相交叉了。比如说现在北大的辛德勇、韩茂莉本来都是史先生的学生,然后到了北大工作。侯先生也有学生,后来又报了史念海门下,所以因为各种原因,相互间有交叉。发展到现在,我们复旦历史地理这个点人最多、最全。北大侯先生那边,他社会事情太多了,北大历史地理现在人很少。史先生那里人倒很多,但老人家老当益壮,一直在一线,流失出走的人也很多。
其实国外也是一样,所谓学派就是有一个传承,但是学派不等于就不变,在历史的长河里,开枝散叶,因为历史遗迹不断被发现,研究的路径有迁沿,原有的历史结论被推翻和重写。不同的老师和学生,不同时代的传承,各自的兴趣和特点,认知与看法的不同,也会产生分歧和游离,学术研究由点到面,会变得丰富、茂盛、复杂。所以师门会大于学派,大于专业学科。
张英:我以前采访《剑桥中国史》明史卷的主编和撰写者,他们会经常强调自己和《剑桥中国史》前几卷的不同,自己和老师们在历史认知、方法上不同以及他们在历史结论上的颠覆性。他们的师承关系好像不会因此受影响。
葛剑雄:顾颉刚先生的特点,他是很开通的人。他能够接受“学而不同”,不要求下面的人一直玩结论和定义。他和谭其骧先生的关系最早就是从争论开始的。就是在课堂上,谭先生发现了顾先生讲课时的错误,跟他争论,提出了自己的意见,然后顾先生鼓励谭先生,去做研究文章。
谭先生在本科的时候,反而是受潘光旦的影响比较大,讲人口、讲移民、讲民族这些。他的博士论文名义上是顾颉刚指导的,其实顾老师管都不管,都是靠自己写的。博士论文本来准备写中国移民史,先写湖南篇,是这么来的。顾颉刚看了论文觉得行了,然后就博士答辩了。根本从头到尾,顾颉刚没有管过他写一个字。
西方的情况和我们不同,美国的情况跟欧洲又不同。欧洲往往是产生一个学派,就会持续发展延续下去,所以欧洲基本上都是费正清的学生。我最后一次见费正清,就是在他学生的家里面,学生请老师来做客,还是联系很紧密的那种关系。美国比较特殊,像哈佛规定不留学生当老师的,所以杜维明都是到外面发展,你有成就以后,哈佛再请你回母校工作研究,都是这样的模式。
在学术研究上,西方重视不同意见。学术观点不同,他们认为很正常。比如费正清,我跟他讲起某本书,作者是他的学生。但费正清说这个学生可不赞成我的观点。哪怕这本书的序言是费正清写的,观点也可能和学生不同,这样的分歧会在一本书里出现,就是这样的关系。
美国学术界有个本领,他们比较善于炒作学术概念。动不动有什么学派,什么新清史,层出不穷,花样百出,其实这个学术概念是个很宽泛的概念。我们就把它们看得太重要了。有人认为新清史学派怎么怎么了不得,但这个学派很简单,要研究清朝,一大半内容要放在研究少数民族,满族和蒙古族上。
张英:你们师门之间的关系怎么样?会有这样的学术分歧吗?
葛剑雄:顾颉刚先生,这个人很了不得,才华横溢,学问大,人非常好,但是顾先生脾气坏极了,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合作的,包括他的学生。
我跟我老师谭其骧写传记,也讲了他遇到的他们之间的矛盾,比如说他跟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上其实是有很多分歧的,但是以前一般人都不讲这一点。顾先生跟谭其骧关系闹僵了,甚至在日记里讲,谭其骧本来是很有前途的,他是嘉兴人,嘉兴人喜欢玩,所以将来肯定没有前途。实际上顾先生是感情用事的,他一度称赞谭先生是最好的学生,但是谭其骧后来一直跟他闹得意见不统一了,他觉得没有前途了。
而且顾先生还有一个缺点,就是很容易听人家的挑拨离间,有些学生就专门在他面前挑事,说这个人那个人不好,他都听得进的,而且容易受影响,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到最后,他们还是君子和而不同,虽然意见分歧,还是师生握手言和。
顾颉刚先生应学生张维华(当时齐鲁大学历史系主任)的邀请,出任国学研究所所长。他去齐鲁大学是张维华请他去的,结果一年多时间,师生就反目为仇了。张维华说,要不就你走,要不就我走,没有办法合作下去了,后来顾先生就走了。
但有一件事,顾先生人品非常好,当年张维华在燕京大学做顾先生门下学生的时候,家里经济困难,书念不下去了,跟顾先生告辞,说自己要退学了。顾先生问清楚原因,对他说:你不要退了,我正好有一笔奖学金给你,可以念书念下去。那么好,张维华在燕京大学念到大学毕业。他一直以为当时自己拿的是奖学金,其实根本不是,是顾先生自己的钱,资助他读完大学的。
顾先生人品非常高,跟张维华闹到这样,从来没有点破:我对你有恩,奖学金这个钱其实是我的钱,一个字都不讲。等到顾先生晚年,他的助手整理顾先生日记,把日记这一段抄下来,寄给张维华,他才知道当年的事实真相,心里很后悔,觉得非常对不起老师,写信跟顾先生道歉,并且对他表示感谢。到了快八十岁的时候,师生和好如初。

 招商合作
招商合作
 供应商入口
供应商入口
 帮助中心
帮助中心
 网站导航
网站导航
 合作品牌
合作品牌
 个人中心
个人中心
 订单查询
订单查询
 我要提货
我要提货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最近浏览
最近浏览